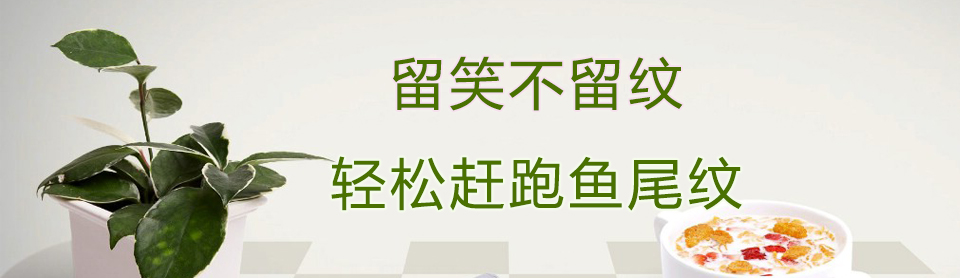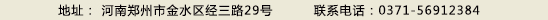盐池额头上的皱纹3
讲堂题字:党英才
盐池额头上的皱纹
3
盐池境内的壕堑如同饱经风霜老人的褶子,由东向西布满额头,它们从黄土地沙漠中直接冲出,起初都很平漫,走着走着便深邃了起来,在丹霞地貌刻下了深深的印痕,让藏埋在沙漠深处的红色的层岩彰显着各自的个性,书写着不同的历史,不同的文化。
离开王记沟,我和官河先生再次向北寻找。向北的高利乌苏村是盐池紧靠鄂尔多斯的一个行政村,其北侧有一条东接榆林,西达宁夏,被商旅穿行多年的北大路。如今的北大路已经静静地卧在草原中,而有关北大路的故事却永远刻在索布边地人的脑海里。
清朝末年放垦大臣贻谷被派到鄂尔多斯放垦黑界地时,神木厅组织了大量陕西神木、府谷、佳县、榆林一些饥寒交迫的百姓,以走西口、刮宁夏的形式寻找生活出路,这条东西连接河套地的北大路为刮宁夏的移民者踏出了生活的希望。看着一个个、一群群从贫瘠苦甲的榆林安置在黑土地上的移民,居住在边里的百姓也开始眼红。多少年来,他们也都曾向往过这片土地,想把这里变成他们发家致富的希望地,只因一道边墙、许多禁令遏制了他们的想法,看到日日移民过来的百姓,他们也动了起来。年左右第一批赶着一大群羊移过去的是冯万仁和张永生,不久一个个寻找出路,寻找生活和栖息地的人们也奔波过去。
从油坊梁流下的沟里已经干枯无水
十三岁的俞喜喜(大名俞文勇)严格意义上说不是参与放垦的,出生于名门后的他,不知祖上在什么时候丢弃了官爵,丢弃了利禄,从广武营逃到灵州城,又从灵州城落难到安定堡。俞喜喜的祖上是名震宁夏的俞益谟,康熙十四年(年),陕西提督王辅臣为响应吴三桂北上兵变反清,在攻陷兰州后,派遣总兵李国良攻破靖边、定边。驻守在花马池的副将朱龙见吴三桂、王辅臣已经叛清,串通定边县的周世民(周四儿)、贺桓和李国良一起占领花马池、安定堡。新任陕西提督的陈福驻守在灵州城招兵买马准备收复失地,刚刚入士的俞益谟跑到灵州投奔了陈提督,参加了收复惠安堡、韦州堡、安定堡,和围攻花马池的战斗。在攻打花马池时受到蒙古索诺慕贝勒下各台吉兵马勇士的援助,战斗结束后,陈福带着俞益谟等部下把索诺慕贝勒送过边墙之外,这事却让康熙帝坐卧不安。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蒙古王爷兵强马壮成了康熙心中最危险的一股军事力量,遂指令严格封锁鄂尔多斯,沿长城边外五十里宽的“黑界地”,不允许汉人进入垦种,也不许蒙古人进入游牧。
俞益谟从黑界地边离开宁夏,走上广阔的镇压反清的战场,最后以赫赫战功赢得两江督标中军副将的红顶子。多年后,他的后人俞喜喜领着十一岁的弟弟沿着他走过的路,从广武营到灵州,再到安定堡,闯进了“黑界地”揽工放羊。
贻谷在鄂尔多斯右翼中旗(今鄂托克旗)的放垦还没有推开,就遭到反对放垦的“独龙运动”,从山西、陕西前来淘金想通过放垦获得土地的人,成了边外的流浪汉,俞喜喜也被裹挟到等候放垦的队伍中,成了不知所向的“流民”。
高利乌苏的土地属于八十一对一只牛换回的地,年前的那次匪患,八十一对一只牛的主家大多遭遇不测,土地荒芜了几十年后,居住在阿拉庙的王爷趁机收回了一些“无主地”,民国初期趁着北京政府走马灯般的换帅之机租给过边找生活的“流民”。年幼的俞喜喜无权租赁土地,只好领着弟弟从安定堡到高利乌苏、路记梁、侯记坑一路向西,当他走到李华台时,被一户从麻黄梁过来的孙姓人家收留了,。孙家老俩口略有家业但无儿子,聪明勤快的俞喜喜在孙家揽工后,深得孙家老俩的喜欢,他们可怜这俩无依无靠四处漂泊的孩子,提出要收养俞喜喜的弟弟,年龄稍长的俞喜喜不忍和弟弟骨肉分离,可又不想让弟弟跟着自己流离失所,考虑再三还是决定把弟弟留在了孙家,从此,俞喜喜的弟弟改俞为孙,为了不忘自己是俞氏后裔,改名叫孙俞德。
孙家老俩将自己的一块地分给了俞喜喜,想让他也有个固定的安身之处。然而倔强的俞喜喜在李华台栖息了一段时间后,离开李华台一个人顺着一道沟经侯记坑、路记梁、段记塘、井沟向西流浪,寻找自己的安身地。
这块尚未开垦的处女地,极目空旷黄沙满地,一入冬,砂砾随着西北风犹如蛇一般地向前爬行,枯黄的草原上几十里看不到一户人家。他沿着弯弯曲曲的沟壑一路向西,走出沟脑七八里时发现了一户周姓人家,疲惫的俞喜喜伴着寂寞的周家,在沟脑的一个沙坎下安置下来。
清政府在飘零中瓦解,北洋政府忙于走马换将,失去依靠的鄂尔多斯王权也攥不紧了,西协理、管家,或一些与王府没有任何关系的人打着王府的招牌经营鄂尔多斯。
根栋原本是一个喇嘛,曾在北洋政府的军队里混了几天连长,回家后凭着活络的头脑云游在鄂尔多斯、定边、盐池一带。云游中他看准了索布边地这块无人经管的土地,在年的一天,召集了几个人骑着马开始在索布边地招摇放地,周家给根栋出了几两银子,租种了沟脑上的一大片土地,然而还没等周家把籽种撒进地里,这块地又被鄂尔多斯右翼中旗王爷府的管家们为了偿还,清朝末年王爷府为帮助朝廷赔偿“庚子赔款”欠下董福祥、高士秀、李照生等人的银子,把这块土地抵押给金积镇的董府。周家花了银子没有种上地,眼望着那块地荒芜在风里。为了生活只好在沟里开了一方土地种下小麦。
几年后背着担子刮宁夏的王万荣领着儿子居住在这里,他们把从家乡带来的熬糖手艺发挥出来,在这里开了一家糖坊,又从董府管家张永生的手中租了一块地,把种子连同希望一起撒进地里。
头脑活络的周家见周边居住的人吃油困难,在自家门口开了一家油坊,然而这里居住的人确实太少了,油坊终因居民太少、入不敷出而歇业,几经折腾后周家无奈地搬走了,在他家住过的地方,只留下了一个称作油坊梁的庄台子。
油坊梁的地势较高,表面是茫茫黄沙,沙下是一层一层的红砂岩,一年四季的雨水按照水往低处流的自然习性缓缓地流淌着,不知流淌了多少年,流淌的水冲开了流沙,冲坡了黄土,把属于丹霞地质的红砂岩也冲起了一层又一层,弯弯曲曲地沿着俞喜喜的来路冲了下去。
流水冲开了八十多米宽的一道水路向东流到井沟,一进井沟村土质从鄂尔多斯台地的砂石突然变成了红石页岩的丹霞地貌,流水在坚硬的岩石面前犹豫地打了个旋转,继而在后浪的推促下向前冲去,湍急的水流把页岩冲开二十多米后狠狠地砸了过去,久而久之在收紧水口的地方向下冲了一道深壕。
整个沟中见到唯一一块玉米地
井沟也是索布边地的一个小山村,年以前这里空无一人,最早来到这里的任八在沟畔山坡上挖了一个土窑,盖上毛柳、铺上沙子就窝在了沟崖边,几年后他等来了一户李姓人家。
年盐池县城边黄记圈居住的黄清泰一家辗转搬到了侯记坑,搭起一座小院在黑界地上养羊放牧,这时候的侯记坑、索布边地到孙家墩只有6户人家,在大户人家是张永生和冯万仁的带领下,放羊多只羊,养牛马各头(匹)。年虽然董家收到王府顶账的土地并没有放垦,居住在索布边地的6户人家却每家都占有大片土地,井沟的地就是被黄清泰所占有。
民国十八年,城西田记掌南梁李文秀的几个儿子为了生存在青山、北大池等地分散打工,他的三儿子李进跑进索布边地的侯记坑给黄进泰家揽羊。有一年黄家遭遇土匪,黄进泰翻墙逃离时不慎将脚崴伤,李进看见后把黄进泰背了出去。年,黄进泰为了感激李进,将女儿嫁给了他,同时把井沟的一块土地划给了李进。
有了土地,有了妻室就有了家,李进把家安在了井沟。年李进的父亲李文秀去世后,孝顺的李进送走父亲把母亲和在外打工的弟弟接到了井沟,一家人除了耕种黄清泰划来的土地外,又借种汪寡妇(丈夫汪天寿)的一块地(不出租子),从此在这道毛乌素沙漠边缘的沟畔边扎下了根。
井沟的沟道是最典型的丹霞地貌沟壑,土质坚硬,沟道狭窄,一层层不同质地的岩石被从油坊梁流下的溪水打击的光滑红润。这沟在年以前是长流水沟,一年四季从不断流,自年的大旱之后成了季节河,夏秋两季河水潺潺,冬春之时干涸见底。沟水异常苦涩,吃水要到数里之外去挑,即使用它饮牲畜、饮羊,他们都会拌着嘴、龇着牙、摇着头艰难地喝下去。
来到井沟看早已干涸的水沟,我想寻找这个村的熟人李凤书,官河先生得知我去井沟村要找李凤书时,高兴地对我说:“他是我的表舅,自我搬进城已经多年没见了。”说着他要给表舅买点礼品,然而在地广人稀缺少人烟的索布边地哪来的店铺。中国人讲究的是礼仪,盐池人讲究的是家教和门风,官河的母亲和李凤书是表姊妹关系,官河见到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张玉凤时,左一个舅妈长,右一个舅妈短时,使我一下看到了盐池人辈辈传承的家风。
李凤书和张玉凤夫妻是我在年代认识的熟人,他俩曾热心地收留过一个离家出走的小女孩,最后还是我和赵含宁联系新消息报社的几个记者帮女孩找到了家。二十多年过去了,张玉凤明显衰老了许多,昔日名震索布边地的铁姑娘,如今要坐着轮椅出门。
坐在轮椅车上的张玉凤
李凤书是李进的侄孙,他家的根在这里已经扎了90年,张玉凤是随着油坊梁沟里的水缓缓地从上游流下来的。她的爷爷张全全是八步战台人,早年略有家产,民国初年不知何卖光牛羊和弟弟一起跑到了毛卜剌堡,混了几年也搬到了侯记坑。几年后张全全的弟弟在蒙口湾被人打死后,张全全在侯记坑养活不了自己一家,万般无奈只好休妻,妻子带着一个儿子改嫁到麻黄山的范记畔,他自己领着三个儿子逆水来到了井沟。
小小的索布边地收留了众多生活所迫流离失所的人们,那道从沙漠中发源的沟水轻轻地流淌着流淌着,上游油坊梁人种过地的沟在年大兴水利建设时被青年突击队和铁姑娘们打了一道坝,开垦了更多的水浇地,直到年代“反革命分子”王庆同被迁赶到这里时还和村民俞汉、张普、王陪元一起“种园子”。
“所谓园子,就是两个塬中间有条小溪,打个小坝把水蓄起来,沿小溪两边开辟出一些小畦,用小坝里的水自流浇灌,种蔬菜,种瓜果。种出来的东西。分给社员吃掉一些,拉出去卖些钱,为生产队增加收入。”
井沟村昔日的蓄水坝无水可蓄
再次来到这里,王庆同教授心中的“园子”已经成了他心中的记忆,沟里的水已经干枯,再也没有往日“泼瓢大雨后的山洪顺沟而下冲进园子,俄而成为铺天盖地狂奔的洪流,呼啦啦呼啸而至。”的景象。井沟村打的蓄水坝早已张开了大嘴而无水可蓄。
光阴荏苒,一道沟断断续续地流淌了数万年,沟边的景色也历经无数变化,沟边的故事也在风雨中发生、雨夜里迷失。自年索布边地有记载以来,沟岸边居住的百姓也从年阿拉庙王爷府指派王秉智管辖的4甲6户人家,发展到3个自然村。沟里的水从油坊梁曲曲廻廻地流淌到八里河湾,而沟里的人却流向华夏各地。
喜欢就请
转载请注明:http://www.tzjhsl.com/zwxc/69543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