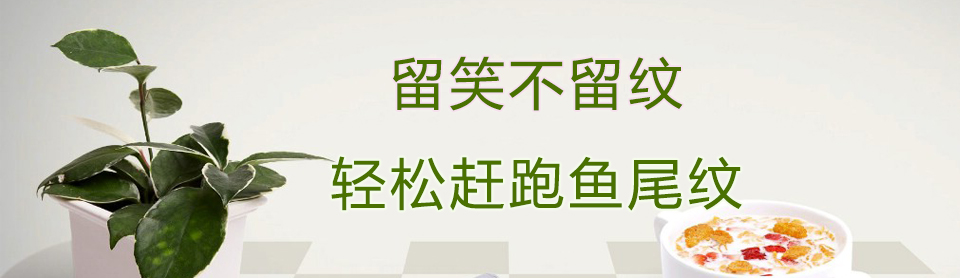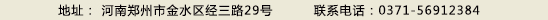盐池额头上的皱纹2
讲堂题字:党英才
盐池额头上的皱纹
2
听说我到沟里调查采访,有人说:沟有啥写的,干涩、心酸、苦难。
是的,盐池大地上的沟的确像这位朋友所说,每一道沟因常年缺少雨露的滋润干巴巴的裸露在草原上,每一道沟都是盐池人生存和创业的家园,每一道沟里都流淌着一段心酸的故事。
我和官队、王院长等追踪到赵记梁北沟经汪记老场,看到这道沟转入路记梁的北边后渐行平缓的一路向东,就又重返到哈日敖包,站在这个旧址上新建的敖包旁仔细阅读敖包的碑文。
哈日敖包碑
敖包是游牧文化的历史遗留物,最早出现在秦汉的匈奴时期,元代极为兴盛。鄂尔多斯右翼中旗的鄂托克黄金家族共建了十三个敖包,由一座主敖包(大敖包)和十二座卫士敖包(小敖包)组成。当年铁木真在统一漠北的战争中,把乞颜氏分为十三翼迎战扎木合,残酷的战争使乞颜氏失去了很多勇士,为祭奠战争中的伤亡的勇士设立了十三敖包。元朝建立后,十三敖包的祭祀又扩大为祭祀祖先和大自然,并有祈求神灵,纳福的意思。明朝中叶曩俺答遣使到西藏迎来三世达赖后,鞑靼部族信仰了藏传佛教,从此在祭祀中有掺入了佛教文化的特征。在祭祀仪式结束后,祭祀者举行盛大的赛马、摔跤、射箭比赛和物资交流、文化体育活动。
敖包从祭祀发展成一个综合性娱乐、商贸、旅游活动场所,每年的农历五月十三日,十三座敖包所在地犹如十三个商贸集散地,十三个运动场,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马背上的民族在生活中离不开马,十三敖包的选址也考虑到祭祀和马匹的饲养,所有敖包都选择在地势高凸、水草丰满的地方,每一座敖包下面都有宽敞的草原和丰富的水源。
哈日敖包两边有两道沟,坡下有宽阔的草原和嫩绿的喂马草。
有水,有草,有活动场所。
离开哈日敖包我们返回到麦垛山,望着这座山丘,我想起乾隆年间宁夏河东兵备道陈履中在《河套志》中所记载的麦垛山“在宁夏府东北二百里,其山出铁,山势高耸如麦垛。”
这山出铁?这山如高耸如麦垛?
可脚下的山并不高耸,也无铁山铁矿,真让人怀疑陈履中志书中的麦垛是否这一麦垛?
从麦垛山向东南可走到赵记梁的南沟,这道沟从赵记梁泻下不远,水势就趋于平缓,沟道浅而平漫,由于两岸土质属于鄂尔多斯台地常见的沙土相拌,整个沟焦黄无奇。我们这次主要考察的是丹霞地貌,这道沟的土质与我们的要求有别,大家在沟里走了一段就放弃了,准备另寻他沟。
官河讲述王记庄台子
欲知山中事,须问打柴人。官河就是索布边地的一个打柴人。6月17日,我邀请官河老先生和我一起再次爬上麦垛山。
七十多岁的官河腿脚利索,精神矍铄,他的祖先本住在边内窑梁上村,多年前发生匪患时,祖父官元邦只身从窑梁逃往河西,过了多年流离失所、节衣缩食的日子后辗转来到边外,得知堂姑父马斗住在大井(在今卢记塘),也投奔了过来,几年后积攒了一点家业后搬到靠近麦垛山的官记台,年官河给叔父顶门后又迁到官记圈,他曾在不同行政村的两个自然村担任过鸡头凤尾官,麦垛山以东地区的所有村庄都留下过他的脚印。
王记庄台子和南边的沟
路上,我告诉官老先生说我向寻找王记沟王氏先祖曾居住过的地方,官先生便把我直接领到王记沟村北边,两道小水沟夹着的一个平塘上。这里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仔细查看也没有三五十年种过地的印痕。西侧有一个小山包,山包下有一块地势较高的平地,这就是王氏先祖住过的院落。乾隆五十八年王姓祖先来到这里,依山面东建了一座院落,从遗留的房基来看院落的面积不大,地基上还能看出三四间正房和两间耳房的印痕,在房基之外还有一道院子。官河先生告诉我,向东一百多米处还有一个院子,但我走到那里看不出一点痕迹。
王家自乾隆五十八年过来到废弃这座院子在这里居住了将近90年,90年的生存与繁衍,应当留有更多的住宅,但在周围我们再也没有找到遗址。
王家占有从王记沟向南到边墙根的大片土地,过着广种薄收、四野放牧的日子,然而在他们平平静静地度过90多年后,一场匪患让他们家破人亡,惊慌跑脱的人几经磨难最后落脚到边墙脚下的青阳井,这里只留下了王记沟这一地名和遗留有石块、破缸片的庄台子。
在王氏房基地的南北两边各有一道发源于王记沟西山梁,被雨水冲击而成的水沟,窄窄的只有三米多,已被积沙淤平,看不到一点水流的痕迹,但多年前这里就是他们的生命之水,曾养育了第一代闯入黑界地的人。
离开王氏房基,我们向北寻找真真的王记沟。
再向北转出多米,有一片平整的田地,穿过田地在一个山峁下一个深沟横在我们的面前,从田地下沟有一条路,路面很宽,但下去后无路可走。我们把车停在坡上徒步走了60多米来到沟底,这是一道冲破丹霞地貌的沟,沟的两侧裸露着一层一层的页岩,依然是红色,依然有些干涩。
王记沟边的丹霞地貌层
这道沟发源于王记沟村西部的山梁,沟底有一道20多厘米宽的沟水,从容地流动着,遇到低洼的地方流水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不大水池,池水清澈透亮。
有流水当有水源,当我们追朔到它的上游时,看到潮红的岩石层中羞涩地低着头,应当有水眼的地方找不到水眼,只见湿润的岩石层里一滴一滴地往出渗水,渗出的水汇聚在一起便形成了那道流水。
王记沟村沟里的流水
这道沟的东侧是红色的页岩,西侧却是沙地,形成了半沟红土半沟沙的自然景观。
越沟是一面沙坡,踏着松软的沙土地行走了一百多米又是一道沟,这道沟是从官记台流下来的,向东流过多米和我们刚看到那道沟汇合到一起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王记沟。这也是被流水冲刷形成的沟,不知冲于何年何月,沟崖峻峭,沟间有一股流水清澈舒缓。
官记台与王记沟只是一沟相隔,这道沟宽有80多米,有水的地方现在只有一米多宽,今年干旱严重,沟里的水也是断断续续,在沟里还能看到一方方、一块块的农田,只因天旱少雨已经全部撂荒。过沟的官记台村,因对面的地势较高,看不见官记台村任何房屋、瓦舍。只看到有一条路沿着沟坡弯曲向上。
王记沟及对面的官记台
多年前官河的太爷官元邦来到官记台后,占据了沟两侧的土地,每年种地时需要从官记台过到沟南耕种,那时沟里的水是长流水,一年四季流个不停,到了冬天,地面上已经结了冰,沟里的流水还在涌动。夏日里遇到下雨沟里涨水的时候,沟里的水有一米多深哗哗地谁都过不去,只好看着沟那边的庄家荒在地里无法锄、割。民国年间,随着官姓人家的人口繁衍,官家老爷子将一个儿子的房子盖到了沟南,每日里沟南、沟北的人家听着沟里哗哗的流水声却无法使用沟中的水,因为在哪个年代没有人能把沟里的水弄到10多米高的田地里。
年,在那个人定胜天的日子里,王记沟、官记台两个村的百姓在大跃进中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在肩挑人推中,在沟底开垦出一片田地,人们种上小麦、种上玉米,祖祖辈辈靠天吃饭的人家终于种上了水地。
官河讲述大搞水利建设的故事
官河站在沟边,望着已经被人们渐渐遗忘的水地,心里五味杂陈,年他扔掉书包后,参加了这道沟的水利建设,每一块地里都留下过他的脚印,年担任了生产队长,每一块地里他都计算过产量,这道沟曾经承担过全村人将尽一半的口粮。
沟水涓涓流淌着,昔日种植的树已经成才,而那几块在大搞水利建设时苦干整平的水浇地却荒芜了。
喜欢就请
转载请注明:http://www.tzjhsl.com/zwqc/695481.html